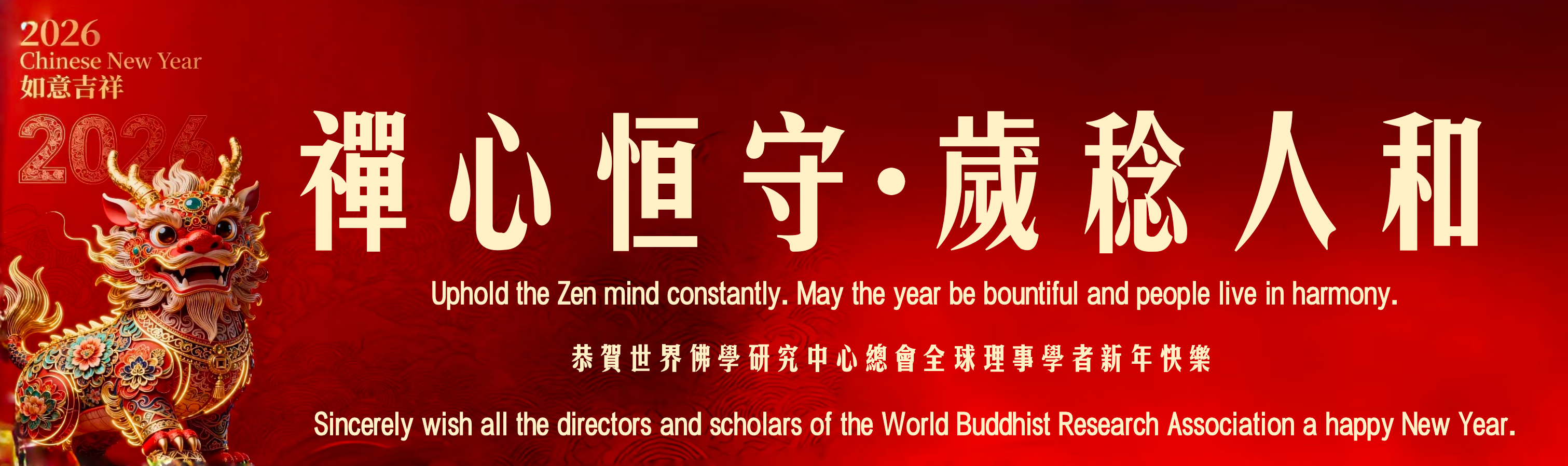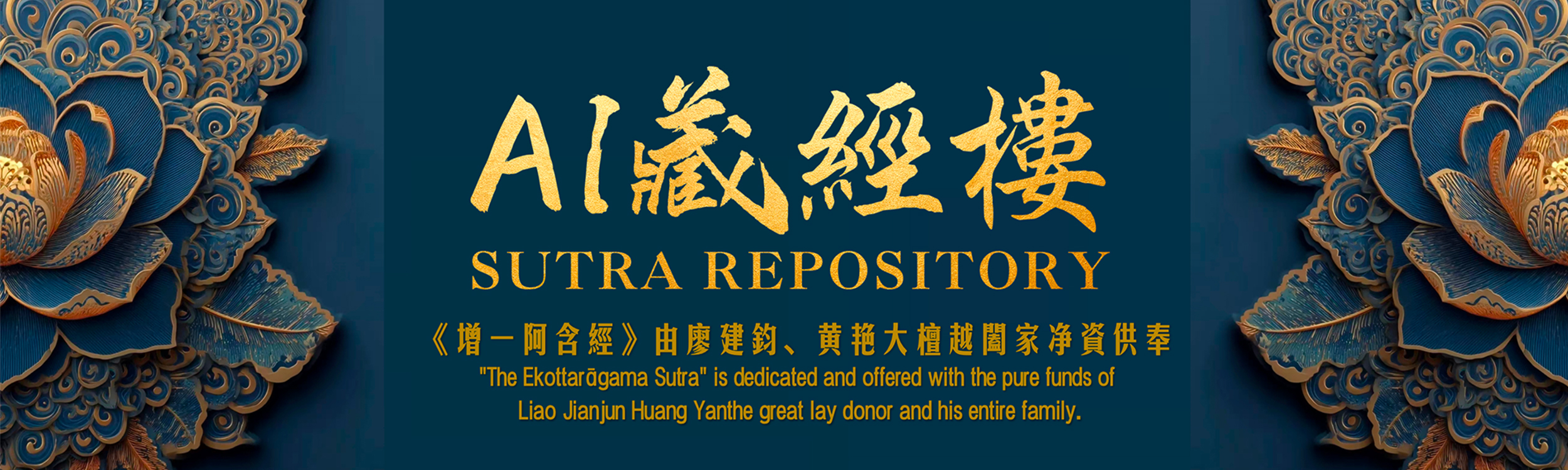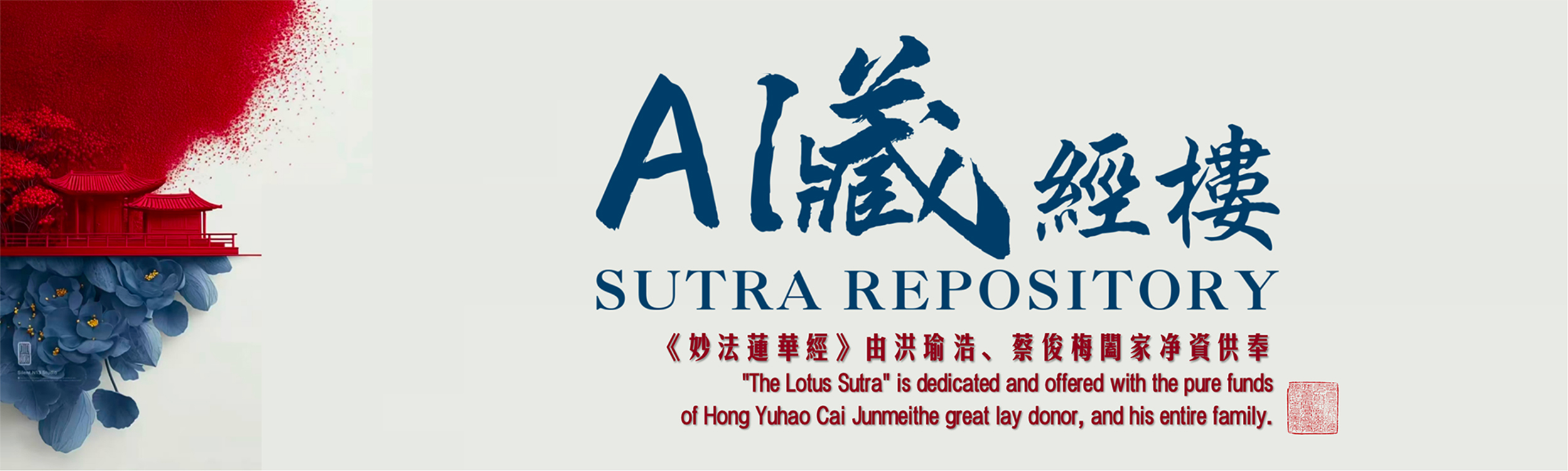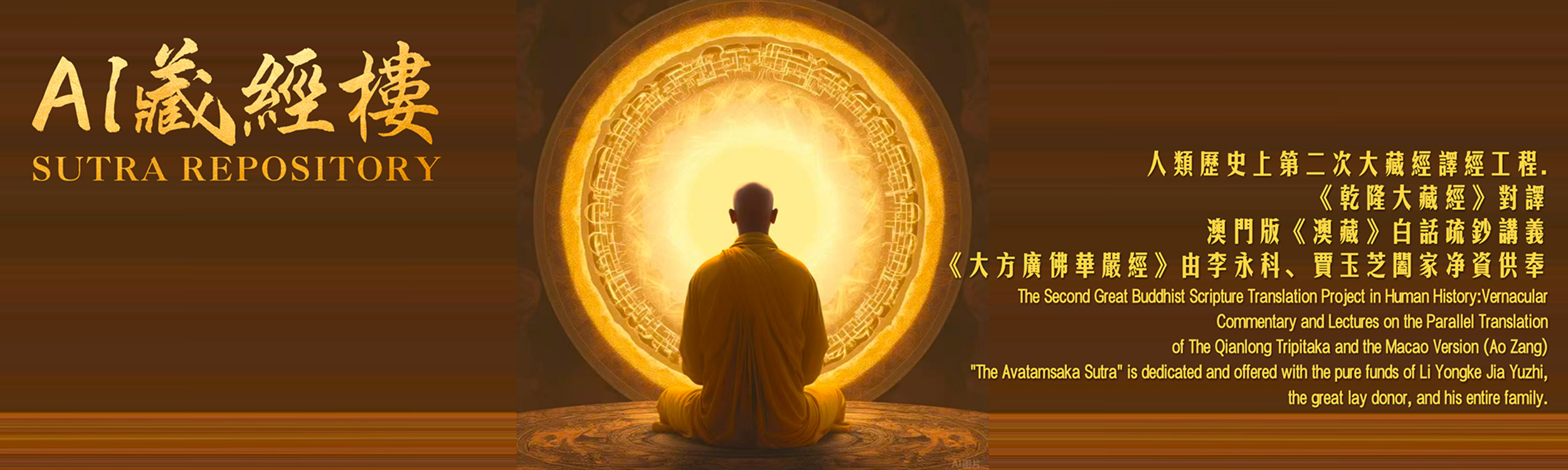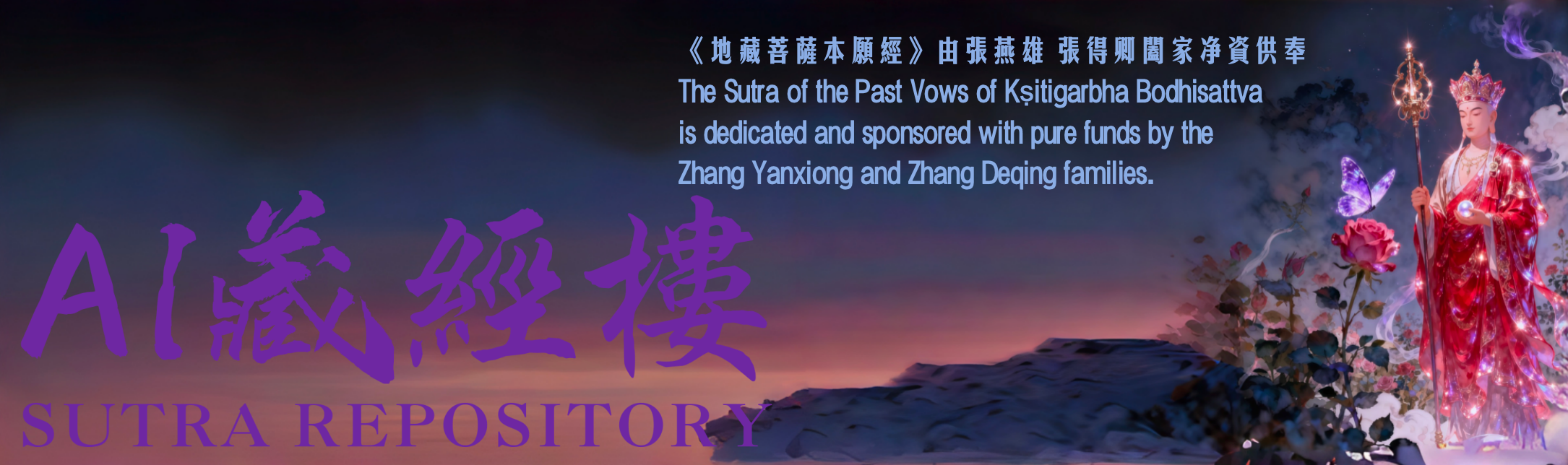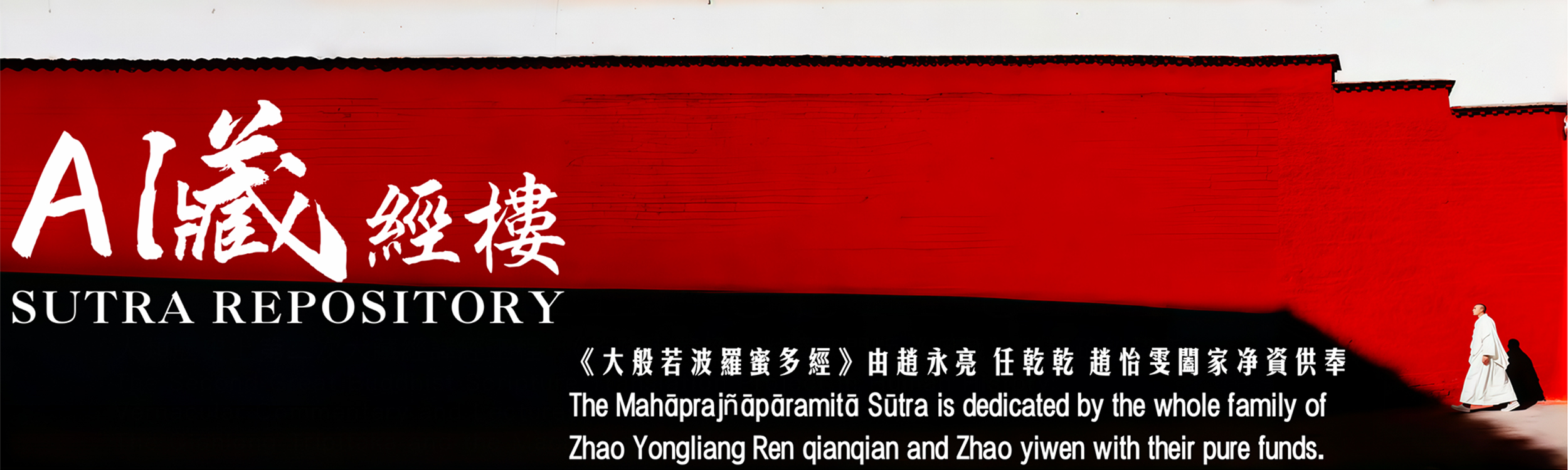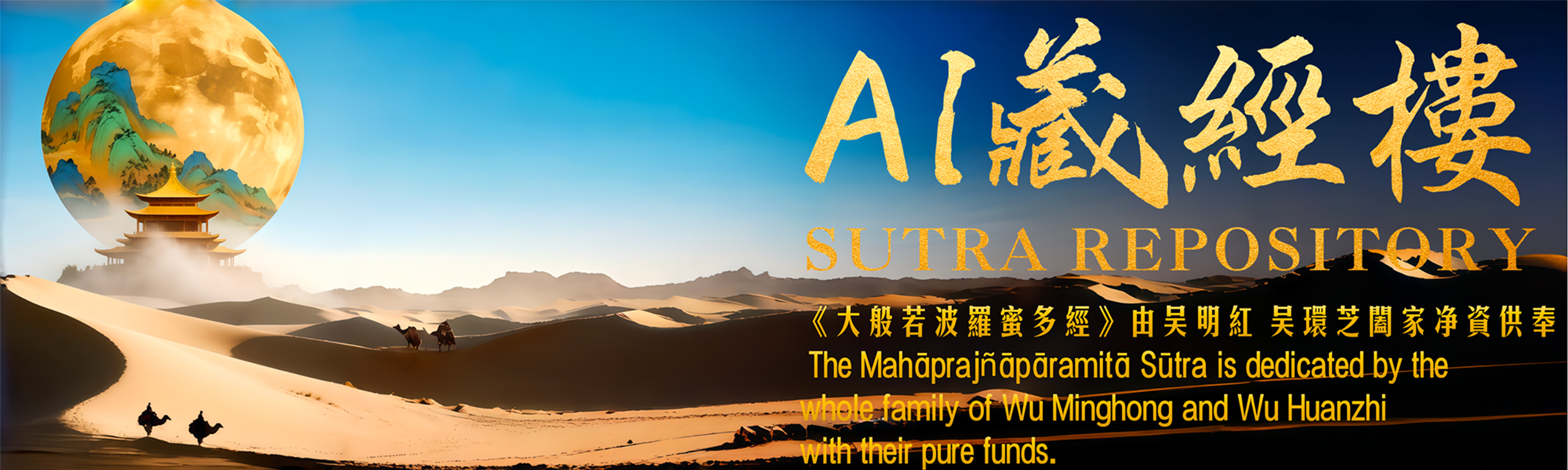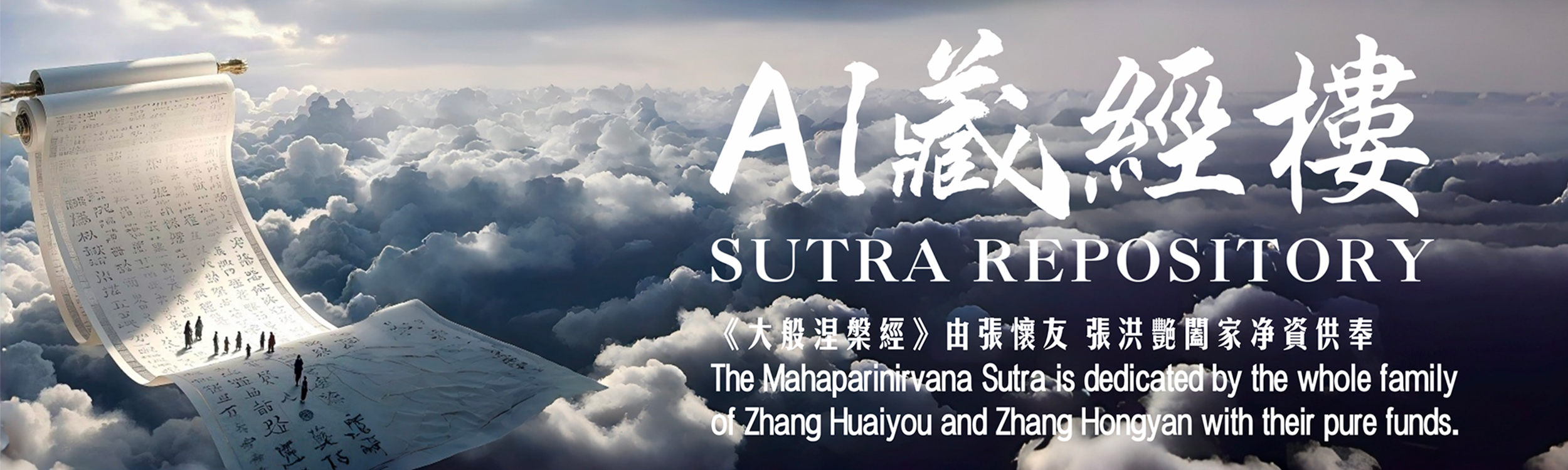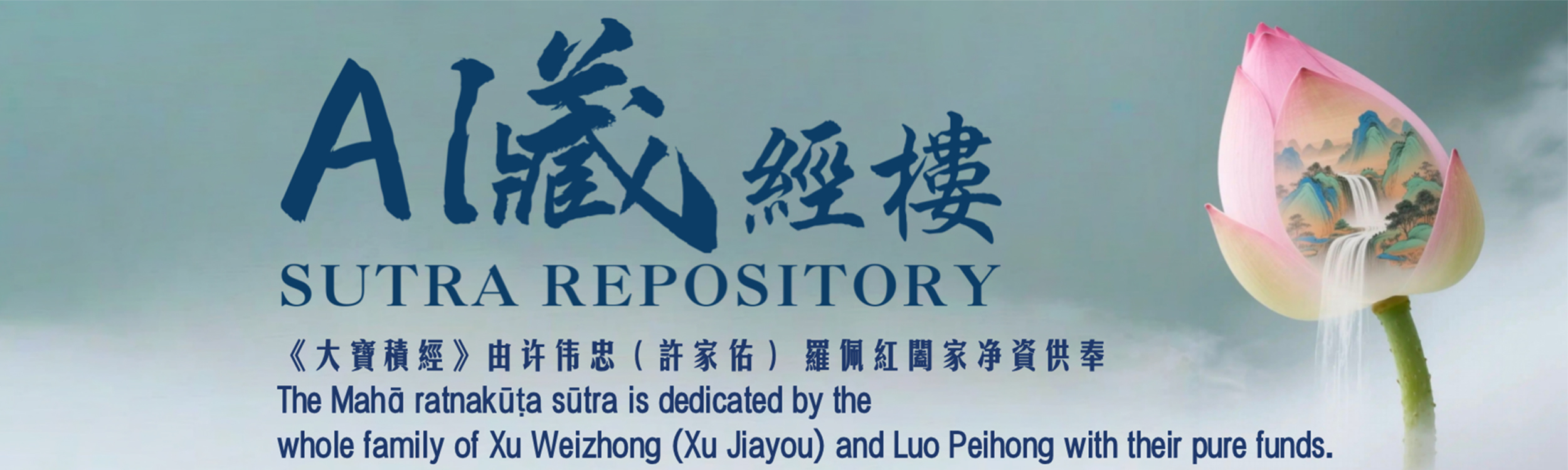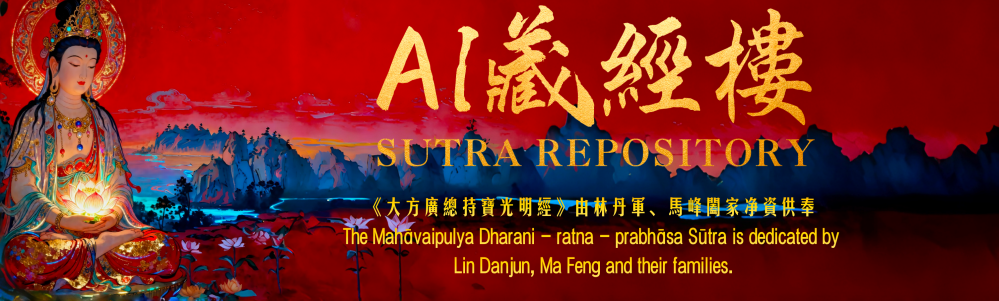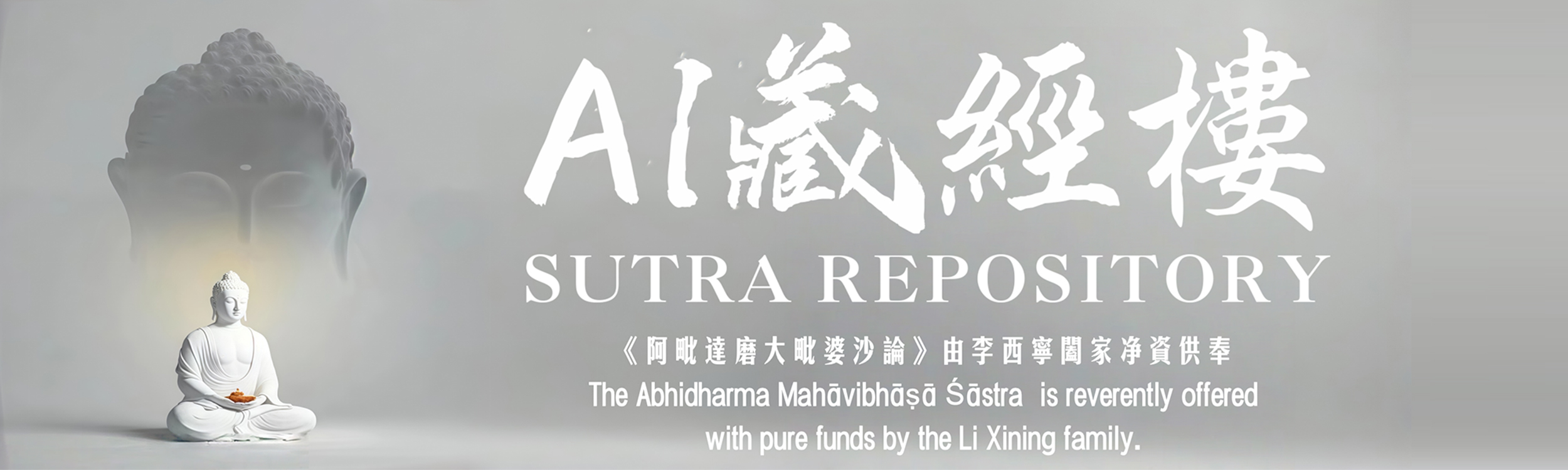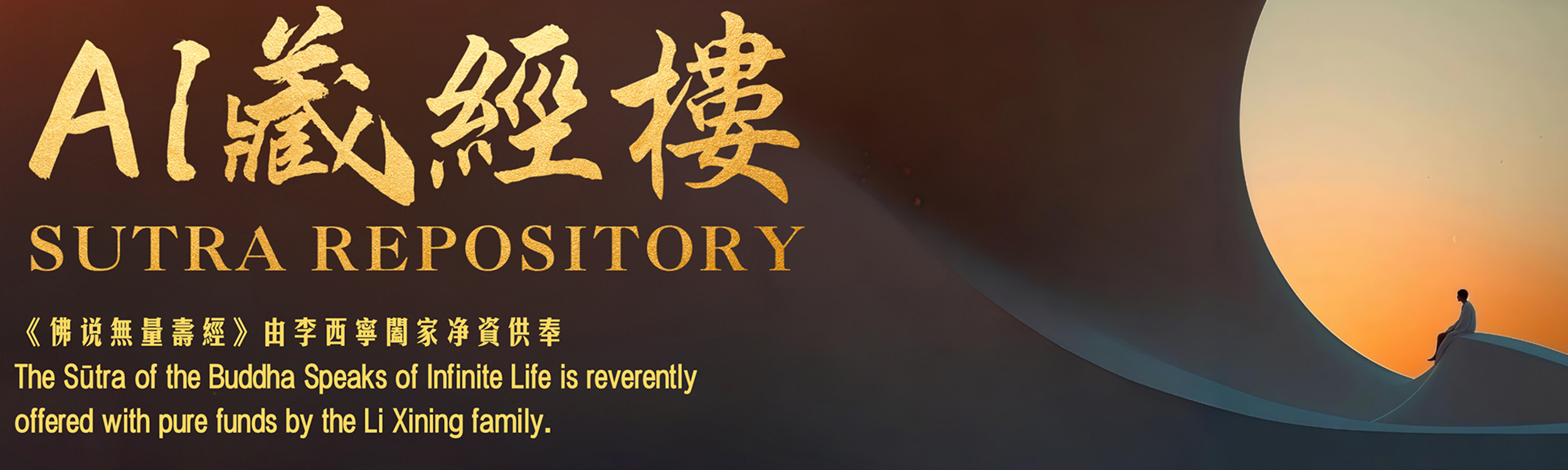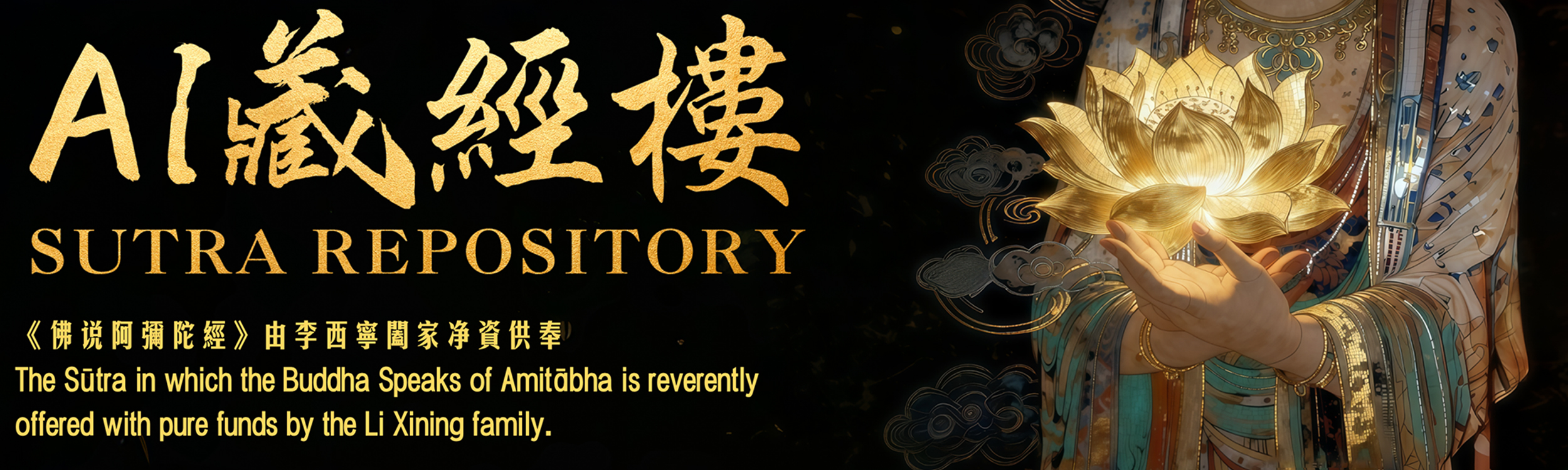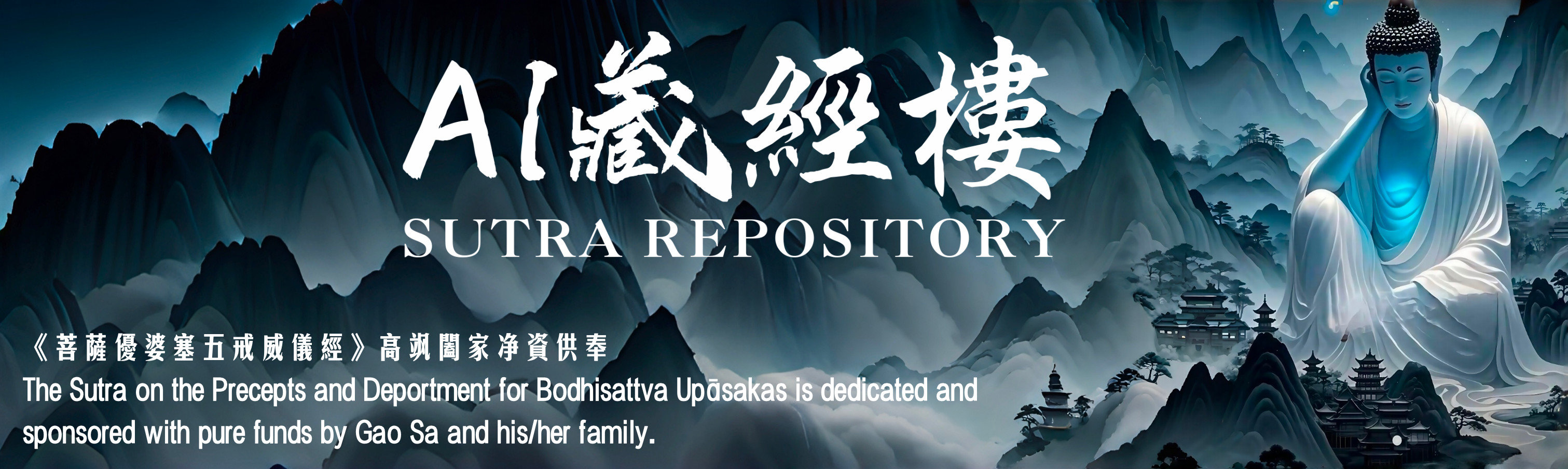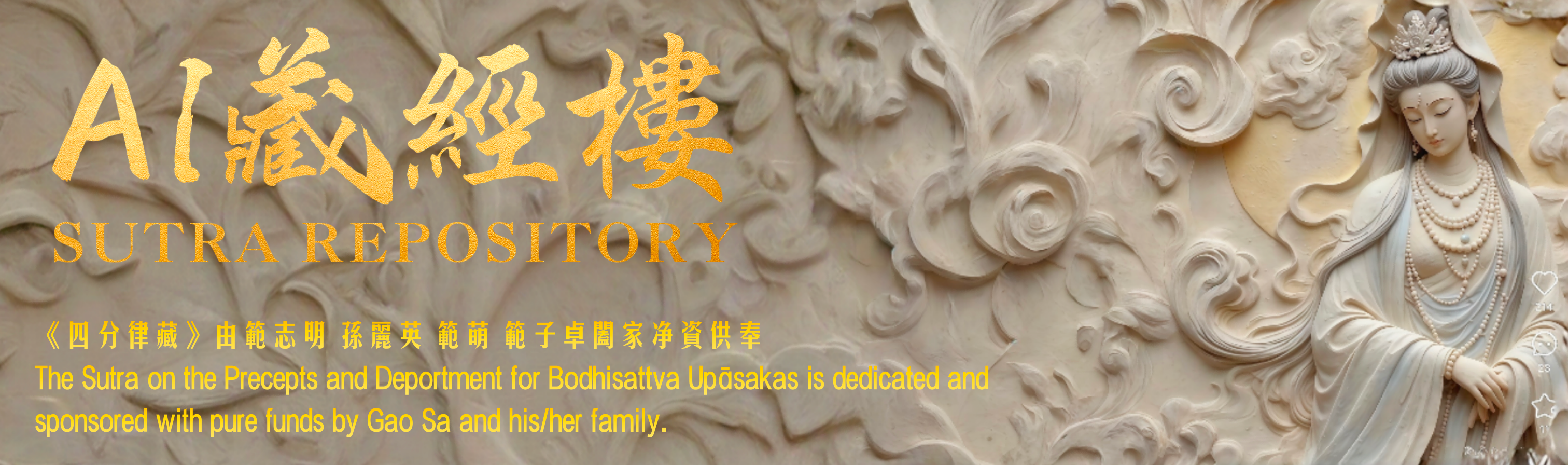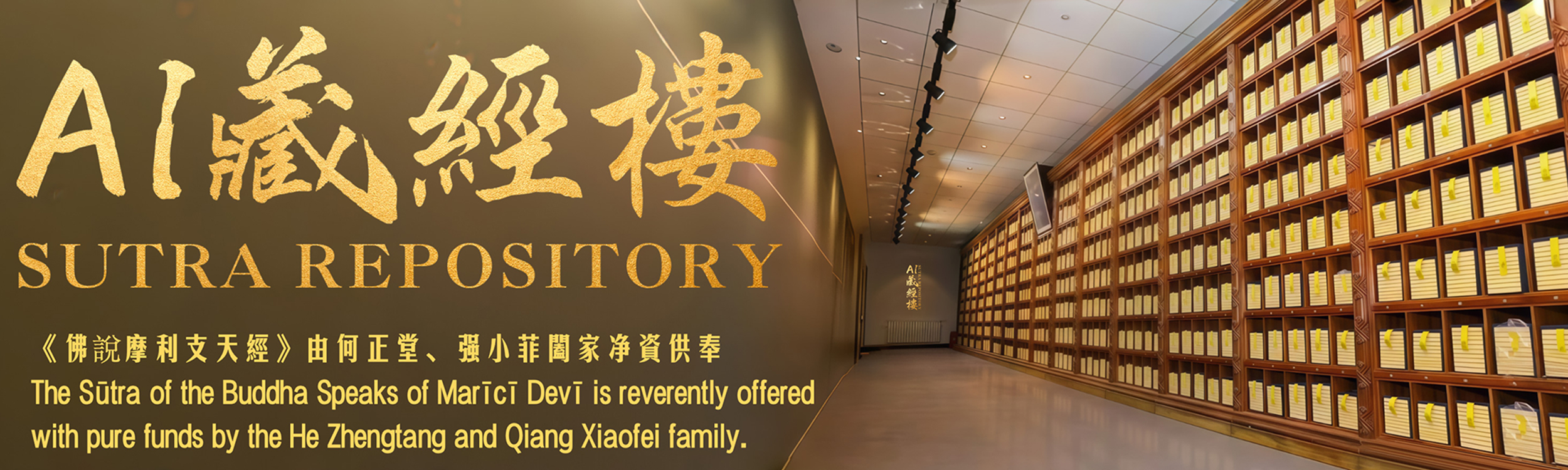|
|
|||||


|
|||||
|
【“澳藏”释名】: 《澳藏》是由澳门佛教总会发起编纂的澳门版《大藏经》白话疏钞讲义,简称《澳藏》。 澳门佛教总会会长上戒下晟大和尚邀请全球百所大学哲学院院长、诸山长老共襄盛举成立世界佛学研究中心(总会)。并发起人类历史上第二次《大藏经》译经工程。 【“澳藏”明宗】: 以白话文为桥梁,贯通文言文的深邃,让千年经藏不再晦涩难懂,使更多人能够接触、理解佛法的智慧。辅以现代科判、注疏,建立AI藏经楼(电子版)与纸质版《澳藏》。这不仅能让佛智契合时代需求,融入当下的社会脉络,更能借助科技的力量,让佛法的传播突破时间与空间的限制。 【“澳藏”辩体】: 《金刚经》有云:“佛言如筏喻者,法尚应舍,何况非法。”昔时,鸠摩罗什、不空、唐玄奘诸大德,发大愿心,西行求法,译梵经为汉文,开启华夏译经先河,为《大藏经》的集结奠定根基。千六百六十九卷经藏,虽仅百部有余得祖师大德科判、注疏,但每一字、每一句皆蕴含着佛陀的无上智慧,如遗珠等待后世之人擦拭、传承。 【“澳藏”论用】: 如今,我们身处AI蓬勃发展的时代,科技日新月异,却也带来人心的迷惑与纷乱。在这末法时代,人心惶惶,正法的传承面临诸多挑战。正如《六祖坛经》中所言:“心地无非自性戒,心地无痴自性慧,心地无乱自性定。”然而现实中,众生多被外境所扰,难以明心见性。此时,佛教界更需秉持务实精神,担当起传承佛法的重任。 【“澳藏”判教】: 释迦牟尼佛一代时教,五时弘传。提出四依法——依法不依人,依义不依语,依智不依识,依了义不依不了义。其中,“依法不依人”最为关键。古德有言:“宁可千年不悟,不可一日着魔。”若不依法而只依人,便容易陷入个人崇拜的误区。达摩祖师一苇渡江,面壁九年,只为传佛心印,他以《楞伽经》为依据,教导弟子不执着于表象之人,而要深入经典,领悟佛法真谛。又如百丈怀海禅师,“一日不作,一日不食”,以自身的修行和对佛法的坚守,诠释了依法修行的重要性。 【三问“澳藏”】:为何续译、为何澳门发起、AI 时代为何人力亲译? 佛陀住世四十九年,说法三百余会,留下的经藏如暗夜明灯,照亮众生迷津。然经文传世需赖译传之力,昔有玄奘大师“乘危远迈,杖策孤征”,译经千卷;今逢AI时代,澳门宏愿盛启人类历史上第二次大藏经翻译工程,定名“澳藏”。此事牵动人心,遂有三问萦绕:为何此事当为?为何择址澳门?为何AI时代仍需人力躬行?今依佛法义理,逐问作答。 一、为何此事当为?——以教材明方向,借经藏续薪火 学佛如入学堂,需有教材引路;求道似涉远途,当以经论为舟。《楞严经》云:“如人以手指月示人,彼人因指,当应看月。”经藏便是“指月之手”,而白话译本则是将“手指”磨得光洁,令初见者能清晰循指见月。 乾隆年间编修《隆藏》,虽集经文之大成,然文言壁垒如隔层峦。大藏经共5600万字、1669部,今传世白话讲义疏钞未满30部,多数经论仍束之高阁——藏经楼中金碧辉煌的经函,若无人能解,便成“死书”;寺庙里庄严的典籍,若不被研读,终是“摆设”。这恰如禅宗公案中“磨砖不能成镜”:若只敬藏经而不学经义,纵是日日焚香,亦难契佛陀本怀。 学佛的核心在“学”与“佛”二字:“学”是随文入观、解悟义理,“佛”是自觉、觉他、觉行圆满。《法华经》言:“若有闻法者,无一不成佛。”可若经义晦涩,“闻法”便成空谈。故译经之事,是为众生铺就“学佛”之路——把看不懂的“古教材”译成通俗的“新课本”,让佛陀教言从藏经楼走出来,走进寻常学佛人的心里。 更有一层深意:皈依本师释迦牟尼佛,当对其四十九年教言“广学博究”,进而“广宣教言”,再以经义为基“广结善缘”、“广种福田”。此“四广”正是续佛慧命的关键:不学则慧命断,不宣则法脉塞,不结缘则众生隔,不种福则善根浅。“澳藏”工程,恰是借译经之力,让“四广”落地,让佛法薪火代代相传。 二、为何择址澳门?——政治护持得因缘,文化交融成沃土 佛法流传,需“内有善信发心,外有因缘护持”。澳门能担此重任,首赖政治引领如北斗定向,再凭文化积淀似春土育芽。 昔佛陀住世,频受国王大臣护持:频婆娑罗王施竹林精舍供僧弘法,阿阇世王归心后以国力护持佛法流通。今“澳藏”工程得到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各级政府机构关注支持并启动盛举,正是“政通人和,法缘具足”之相。澳门享“一国两制”之殊胜,既沐国家关怀,又具社会安定之境——无世俗纷扰乱心,有政策护持助行,恰如《维摩诘经》所言“心净则国土净”,这般清净因缘,最合译经弘法。 更有澳门佛教总会会长上戒下晟大和尚,以“荷担如来家业”之愿,亲自组织编译。大和尚常言:“经藏非古董,是度生舟筏;译经非虚功,是续法命脉。”此语正合印光大师“佛法在世间,不离世间觉”之旨。而澳门本身的文化土壤,更让“澳藏”落地有根:自开埠以来,中西文化在此交融,却始终保持佛法香火绵延——功德林旁梵音未断,普济禅院法鼓常鸣,民众对传统文化存敬畏心,对佛教典籍有护持意,这般“文化共情”,正是译经工程最需的“水土”。 乾隆编藏因皇家之力定名“隆藏”,今澳门续译以地域之缘定名“澳藏”:“隆藏”显威仪,藏于名山待有缘;“澳藏”重普惠,译于现世利众生。“澳藏”拟申请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,更是欲将中华佛教文化的精髓化作全人类文明的精神财富——如《华严经》“一花一世界,一叶一如来”,一部“澳藏”,便是连接古今、贯通中外的文化桥梁,而澳门这方“交融之地”,恰是架桥的最佳支点。 三、为何AI时代仍需人力躬行?——机器难悟言外意,人心方解法中真 今科技昌明,AI能译多国语言,故有人问:“5600万字藏经,何不让AI代劳?”此问未明“译经”之本质:译经非“文字转换”,是“义理传递”;非“机器做功”,是“心法相印”,恰如禅宗“指月”之喻——AI能摹“指”之形,难悟“月”之明。 大藏经之难译,在“言外有真意”。佛陀说法常借“方便语”显“真实义”:《金刚经》“所言法相者,如来说即非法相,是名法相”,若AI直译,只会逐字对应,怎能解“破执”之旨?《心经》“色即是空,空即是色”,AI纵查遍语料,亦难悟“色空不二”之理。古来译经需“译场十德”:除“信、达、雅”,更需“解佛法、明根器、通圆融”——AI无“悟”性,怎解这般深意? 更需警惕“数据反噬”之险。AI译经靠“既往数据”,可大藏经白话译本未满30部,多数是文言原文,AI无“优质数据”为基,便如“盲人摸象”:译“无明”为“没有光明”,不知是“烦恼根本”;译“涅槃”为“死亡”,背离“不生不灭”真义。这便是“数据反噬”——以碎片化、误解的数据为依据,越译越偏,终至“胡说八道”,恰如《楞严经》所言“认贼为子”,以错解为正见,反误众生。 故AI时代更需人力译经:人能悟“言外意”,AI不能;人能辨“真与伪”,AI不能。吾辈今日亲译藏经,既是为众生“做真教材”,更是为AI“种善根”——把精准透彻的白话译本馈予AI,方让科技工具得入“法流”,未来能助佛法广传,而非沦为“误法之器”。这恰如“先有农夫播良种,后有仓廪五谷丰”,今日人力躬行,正是为后世佛法与科技相融“播下良种”,这般“传薪”之事,舍人力而不能成。 “澳藏”五重玄义与三问既答,“澳藏”工程之殊胜可见:为续法脉而译,是“承古”;择澳门而译,是“得缘”;以人力而译,是“保真”。愿此工程顺遂,让大藏经如春风化雨,滋润众生心田,让佛陀教言似暗夜星光,照亮迷者归途——正如《法华经》所言:“愿以此功德,普及于一切,我等与众生,皆共成佛道。
|
|||||
|